六十年代初的一天早晨,大明、小明在去上学的路上争得脸红脖子粗的,这时正好遇见一个路人,路人问小朋友你俩争什么啦?
小明讲我们是兄弟俩,现在是在去上学的路上,刚出家门时妈妈给我们一人一个山芋,是由我们中午充饥的。可哥哥的山芋比我的大多啦,小明讲完了路人还问了大明是这么回事吗,大明一边点头一边嗯嗯嗯的答应。
路人讲要想把两个不一样大的山芋弄成一样大我有办法,说着就伸出他的两只手,示意大明,小明把各自手上的山芋给他来弄平均了。两小兄弟不知路人怎么弄平均了,于是就把各自手上的山芋给了他。
路人拿了两个山芋后先在大一点的山芋上咬了一口后问:怎么样差不多大了吗?小明很公平地讲小的又变成大的了,路人又在小山芋上咬了一口后又问现在一样大了吗?小明又讲大的还是大一点。路人正准备咬第三口时、大明开口对路人讲你不要再帮我们把山芋弄成一样大了,再弄就被你吃光了,并接着说这两个山芋都由我弟弟中午吃了,我早饭吃得多中午饭不吃没有事。
就在路人准备咬第三口时,小明也隐隐约约的好像想起了什么不对劲。哥哥把路人帮他们把山芋弄成一大的真正的目的点破后,小明问哥哥你怎么知道路人正真的目的呢:大明说当时我想起了老师讲的“渔翁得利“的故事了。
大家好!我给大家讲个好听的故事!希望大家喜欢!?
从前,有两个孤儿,从小父母早逝,哥俩好不容易长大。哥哥娶了媳妇,新嫂子进门后,就视弟弟二柱为眼中钉,总是虐待他。
还让他每天都去山上打柴,二柱每天都吃不饱,穿不暖。而此时的哥哥大柱,本来以前对弟弟还好,可是自从娶了媳妇,便惧怕媳妇,不再对二柱好,而且也总是对他呼来喊去的。
二柱为了讨得哥嫂换心,每天都起早贪黑的干活。可即使如此,哥嫂还是看不上他。
目睹他年纪越来越大,已经到了娶媳妇年纪,不想再让他拖累家里。夫妻俩一合计,便要分家,两个人算计来,算计去,地和房子都不舍得给他。
二柱看出来了,便对哥嫂说他什么也不要,只想要那只,从小陪自己长大的大黄狗大黄。哥嫂听了,很是高兴,满口答应了。
就这样,在一个黄昏,二柱牵着大黄离开哥嫂家。他也不知道该去往何处?很是茫然的走着。来到不远的山脚下,想了想,自己动手盖了间茅草房,临时有了安身之地。
此后,每天都上山打柴,挑到集市去卖。由于他勤劳能干,过了不久,就用打柴的钱置办了些简单的家什,日子总算安定下来。
一天,二柱又从山上回家,又累又饿,回家一看惊呆了,屋里的桌上摆着四个菜,还有一壶酒,不知道哪里来的?他太饿了,也就不想那么多,坐下来,狼吞虎咽的吃起来。
此后,日日如此。却说他的哥嫂,看他搬走,什么都没有,想着肯定会过得很落魄。知道他在山下住着,有一天,夫妻俩去偷看了几次,发现二柱房子的烟筒不冒烟,很是纳闷,他是怎么吃饭的?便蹑手蹑脚的扒开门缝一看,顿时惊愕住。
里面的大黄狗在地上打个滚,忽然变成个大姑娘,用手甩了甩,面前的桌上,立刻有了四个菜,一壶酒。
夫妻俩大惊,看着那姑娘变回老黄狗。便喊着:“妖孽”!冲进去,用棍子把大黄狗打死了,夫妻俩兴奋的把那些菜和酒拿走了。
二柱挑柴回家,在路上,虽然累的气喘如牛,但一想到会有酒菜等着自己,心里很是兴奋。可是回到家,看到屋里没有了酒菜,而且大黄不知被谁打死了!不由悲痛欲绝,泪水成河。
他和这条大狗感情特别深!从小就形影不离,受了委屈时,他向它倾诉!干活时,大黄都会陪着他。
只不过,后来搬出来,不知道怎么回事,大黄却是不陪他上山了?他哭的昏天昏地的,不吃不喝好几天。把大黄好好安葬在自家不远处。每天回家,都去坟前坐会,有时候,会买点大黄爱吃的摆在坟前。
过了几个月,坟前长出一棵小树。有一天,二柱不小心碰了树一下,却是哗啦啦从树上掉下来一些铜钱。二柱又惊又喜,连忙拿着铜钱去孝敬哥嫂!
哥嫂又惊又喜。第二天趁着二柱不在家,夫妻俩也买了些好吃的到坟前,然后,两人疯狂的摇树,没想到,却是掉下几块石头,把两人砸的头破血流。
两个人气坏了,拿据把树锯断。二柱回来看到很是难过,便又用树木做了棒槌。有一天,去河边洗衣服,拿着棒槌砸衣服,没想到,破旧的布衣竟然变成了绫罗绸缎,二柱又惊又喜。
哥嫂知道后,连忙来借棒槌,二柱爽快的借给他们。夫妻俩拿了棒槌砸衣服,却是一砸,一个窟窿,气急败坏的把棒槌扔进灶膛里。
忽然,灶膛里喷出一条火龙,瞬间,房子着火了,等到二柱和大家过来救火,大柱和媳妇都已经被烧死了。?
分享故事,最好分享励志的那种,这种故事谁都喜欢。
再不就是爱情故事,这是人类远都读不厌的永恒。
如果你想写故事或是分享故事,多去借鉴一下故事领域的原创作者们的作品。
当然,也可以关注我的头条号或搜索避风卧雪的作品。
我在头条小说频道,正在更新同名小说《避风卧雪》第一卷《生存》。
感兴趣的可以加入书架!
风凰山下有两小屯,一东小甸,百姓多姓马,又叫小马屯。一西小甸,大多姓刘,也叫小刘屯。解放后政府将两屯合并为一村,叫靠山屯。
有一天,这里发生了一场夺子大战。
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。马家有一女,貌美如花,绰号"大洋马"。洋马洋马,就是人人可以骑上。她风骚放浪,待字闺中就丑闻不断。
刘家有一男,天生呆傻,木讷老实,人送外号"傻大瓜"。
谁能想到这两个性格迴然不同的人有一天居然会走到一起,结婚了,而且婚后不久,还生了一儿子。
"傻大瓜"的父亲是靠山屯的老支书,突然有一天被大洋马的哥哥领着一群造反派赶下台,扣上纸帽游街批斗。这下"大洋马"不和"傻大瓜"过日子了,她提出离婚。
"大傻瓜"早就受够"大洋马"的气,头顶上的绿帽子压得他喘不过气,便答应离婚,不过,儿子要由他抚养。
大洋马虽然风流成性,但非常爱儿子,要把儿子带在自己身边。
最后,"大洋马"的哥哥出面,强行把孩子判给母亲。
这下引起刘家众怒。本来,老支书无怨被批斗已经惹起大家不满,现在连孩子也被夺走,更激起民愤。大家一起商议,决定把孩子夺回来。
农历十五,是靠山屯大集,一大早,刘家的探子就探到"大洋马"带着儿子从小马屯到镇上赶集,于是,一群人便装扮成各式各样,拿着家把式,赶到集上。
那"大洋马"领着儿子在集市上溜跶,一抬头,看见"大傻瓜"领着一群人气势汹汹地向她奔来,顿感不妙,赶紧拉着儿子就跑
,一边跑一边大声呼救。
集市上有不少马姓子弟,见此情景,一面派人赶紧向小马屯求救,一面拥了上来,很快,双方的人对峙起来。
话不投机半句多,不知是谁先动的手,立刻陷入一片混战。
混乱中,儿子被人打倒,大傻瓜扑了上去,用自己的身体挡住儿子,大洋马也奋不顾身扑了上来。
等当地公安闻讯赶到,市场上一片浪籍,事后统计,混战中至少有十几人负伤,被立即送往医院接受治疗。
其中儿子流血过多,需要马上输血,"大傻瓜"顾不得自己受伤,二话没说,撸起衣袖就要输血给儿子,医生建议先化验一下血型,他火了,吼道:老子的血和儿子一个血型,赶紧救人。
医生坚持抽血化验,结果出人意料,大傻瓜的血型竟和儿子不是一个型号,也就是说,闹了半天,这儿子不是他亲生的。
他这个悔啊!
黄土高坡蜜月见闻/
老公把我驮在自行车后面,在那缓坡上骑着,朝前看那弯曲的山道盘旋着无尽头。突然,那自行车把一甩,车子朝右偏倒过去,我直接大头冲下地滑了下去!下面是斜山坡,还好不算陡,我半截身子在路上半截身子和脑袋在坡下。老公慌不迭地下来把我拉起,嘴里叨咕着:"糟了,这下给甩到山下去,我拿啥跟我爸妈交代呀‘’!
"今天要把我摔死了,你好好想想怎么跟我爸妈交代吧‘’!我生气地说。这时骑车在前面的他哥慌忙跑回来问摔着没有,我说没事儿!他哥埋怨了他几句,又开始驮着那两个大包骑着往前走。此时他说:"我说哥们,我实在馱不动了,咱俩慢慢走行不‘’?我翻了他一眼:"你那俩包不比我轻,看你怎么也扛回来了‘’!他讪笑着:"呵呵,那玩意儿不是没长腿吗‘’?于是我俩便慢慢行走在那山路上。
路上,碰到了他的一个复原了的战友,两人亲热地聊了几句,那人看了我一眼问:"这是你家夫人吗‘’?他说是。我内心在想:天哪,这么落后的一个地方,竟然有这么文绉绉的语言,把媳妇称作夫人,简直令人难以置信!这与他们那高原红的脸,灰酱酱的耳朵也太不搭调了!转而一想也对,老公毕竟大小也是个军官称为夫人也不为过。
那座无尽头的山不知爬了多久,终于来到了他家门口。还没到门口他就大声喊:"大,我们回来了‘’!门口出来个老头:"这是咱大,快叫大‘’。我张了张口没叫出来,顿了下喊了声爸。公公慌不迭地喊着婆婆:"快,娃都回来了‘’。婆婆颠着一双小脚,把我们迎了进去。
一进门,大伯哥跟嫂子说:快去打盆水,让他们把脸"撕撕‘’!我一下愣住了,怎么一进门就要撕脸,这是什么规矩啊!老公见我发愣,快点呀让你洗脸呢!
那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,我们俩旅行结婚回他家。火车上颠簸了二三十个小时,最终在一个小站下车。腊月的小站,北风呼呼地吹着,几乎看不到几个人。四周看看满眼的黄色,难怪叫黄土高坡呢!
他扛的那两包东西重得不行,我只拎了点自己换洗的衣服,下了车,他走走歇歇,几次我说帮他抬他都摇头,说你不行。有阵他放下我去提了一下,果真提不动。我不知道他那包里究竟都装了些啥。
我们回去的当天,婆婆现给我们缝的新被子,这时我才发现,原来那是他早先就买好的,准备结婚用的被面和被里,包括棉絮都是他自己准备的。真是难为他了从那么大老远的地方背回来。
到家的第二天我早上起来,见院里来了个蓬头的女人,在跟嫂子说着什么,我也没听懂,只见嫂子进屋拿了把梳子给她,她边说话边出了门。我有些奇怪问嫂子女人说的什么?嫂子说她是隔壁家的夫人,上咱家来借梳子梳头的。她家的炕上从来连炕席都没有!我惊诧地下巴差点掉下来!夫人?连梳头的梳子都没有的夫人?最终折腾了半天我才弄懂,他们这里管女人都叫某家的妇人!我心凉了半截,我只当了一天一夜的夫人,弄了半天是个妇人!
公婆给我们准备的婚房是个小高房,上去有自己的小楼梯,比院里其他房子高出小半截。每晚我都先进去睡下,老公则每天与父母哥嫂聊完天再上来。每次上来手里的半导体都是唱秦腔,不知不觉中我竟深深地喜欢上了秦腔。
哥嫂的儿子都五岁了!大大的圆眼睛圆乎乎的脸很好玩儿!我终日带他跳绳、打秋千、弄个笸罗扣家雀……,有时我没在跟前,公公就守在那笸罗前,帮我看着,家雀一来就拉绳儿!
回去的一日三餐多数是吃饼或面条,有时吃大米饭,那种时候很少。我是北方人还挺习惯。公公很细心,一天到晚看着钟点儿让婆婆给我们做吃的。晚上睡觉前,都要让婆婆给我端两个发面饼放到桌子上,怕我饿了好吃。在那住了一个月我都长胖了!
我们在家过了年就往回赶,公婆的眼泪像开了闸的小河!老公告诉我,他们都很喜欢我。
后来,我才知道,为了保证我的吃喝,公婆在女儿那借的麦子,老两口抱着磨棍一点点推出来的面!知道后我难受了好久。最终我还知道了,老公那沉甸甸的两个大旅行包里,装了几十斤大米。
就在我回去的那年,农村土地包产到户了,公婆家的日子一点点好了起来。
有一个真实遥远的故事,是关于我年轻时遇到的一件事。
平生第一次出远门,从大西北到大东北,一连坐了近6天的火车,才到达了目的地一一哈尔滨,是9月份去的,参加一个商业部召集的短训班,参加的名额是我国三北地区的有关下属单位的培训人员,委托黑龙江商学院授课培训。1月放寒假时才能结业。
到了哈尔滨不久,漫长的冬季就悄然而至了。要想出门就得象当地人一样全副武装,皮帽子、皮大衣、皮靴、棉口罩、棉手套一样都不能少。街上没有铲除的冰雪,就象是玻璃一样光滑。有一次我逛街,要走过结冰的路面,正在小心奕奕的走着,忽然,脚下打滑,脚底腾空撂在了地上,当时害怕别人耻笑,也顾不上疼痛,迅速的起身朝前走去,大约走了十多米远,后边一个清脆稚嫩的声音传来,“叔叔,你的手表掉了”,偱声扭头看去,是一个大约7、8岁的小女孩,正气喘吁吁的朝我跑来,手里拿着块手表,我再看自已的手腕是空的,我明白了,是刚才滑倒摔跤时,手触地时表链扣震开掉到地上了,被当时相距不远的小女孩捡到了。
几十年过去了,我仍然记得这件事,倒不是表有多么贵重,而是这小学生纯真的拾金不昧的举动感动了我,心想这个善良可爱的小姑娘定能成长为优秀的人才。
我来讲一个吧,是现实故事的升华。故事名字就叫做《青果儿》吧,毕竟这一切都是从一块青果干而起的。
正文如下:
杨妮从小区大门口回来的时候,她手里拿了一个包裹,只凭包裹盒子的大小和重量,不用仔细看,杨妮就知道,这又是小芳寄过来的青果干了。
应该有六个年头了,每年九月小芳都会寄来一包青果干,她知道杨妮爱吃。青果干是用落下的青苹果做的,虽然不贵,但要找到却不容易。也不知道,这些年小芳是从那里找到的,太难为她了。
杨妮现在是单着的,领着孩子两个人过。六年前和那个人离婚后,她就回到了家乡,工作也不如意,还好孩子学习努力,懂事较早。六年前的那些年,就像一场梦,杨妮总是不愿意回忆,可这袋青果却又勾起了那些泛潮的往事。
杨妮知道,小芳并不是故意的,她是在心疼自己。回想第一次见到青果干的情形,杨妮不由得苦笑一声。唉,还是年轻嘴馋啊,十多年了,第一次尝在嘴里,酸酸、甜甜,涩涩的感觉,再也找不回来了。
那个时候,那个人还是一个好人,高高的个子,挺拔的如同一棵长在山头的树。杨妮是山里的孩子,见过太多的树,唯独不曾见过这样一棵,一上来就让人想要依靠的树。
母亲曾说,女人要自立,不能太依赖男人,杨妮信了。可见到这个男人拿出的青果干后,她又把这句话忘了。
第一次尝到这种神奇的小零食,杨妮就有了自己做的打算。谁知,那个人用舒缓的男中音讲过青果干的来历,她就知道自己是没得救了。
杨妮不相信一块小小的青果干,竟然会这么麻烦。直到大学二年级的暑假,亲眼见过青果干一片一片的变干,她才相信,这不是谁都能吃到的美食。
上等的青果干,必须要用农历四月份落下的青苹果。先要把落果收集起来,然后在果园里挖一个三尺见方,两尺深的大坑。用两层塑料纸把落果紧紧包裹,再填上土,种进苹果地里。
一个夏季的果香熏陶和日照雨淋,苹果树盘绕纠缠的根须提供养分,种下的青果在阴凉的地下慢慢的发酵酝酿。这个过程一直要持续到九月,摘掉苹果的果树只剩零落的黄叶、红叶,可根须还在生长。
闲下来的农人,悠闲的刨开土,打开封闭的塑料纸,于是经历漫长等待的落果再次成熟了。咬上一口,酸酸的、脆脆的、甜甜的、涩涩的,那种诱惑不是谁都能抵挡。
可这样美好的果子也是有缺陷,就像世间存在的美好,总是很短暂,熟透了的青果儿也只能保留两三天的美好。于是果农有了新的方案,把果子切着一寸厚的牙片,一个个穿在三年生的狼牙刺上。
接下来就是唯一的了,必须有平地土窑,阴凉通风。扎在狼牙刺上的青果牙儿还要再住上一个月,慢慢的风干,把最后的一丝水分挤掉。一片一片的青果干成形了,弧形的身躯,淡绿色的果皮紧紧贴着,果肉成了透亮的浅黄色。也是这个时候,才能在来年五月之前,尝到苹果年轻时的味道。
那个人来自果乡,于是杨妮整整四年的大学生活都被这青色的果香环绕住了。小芳是杨妮的闺密,总是嘲笑她,说她小小年纪不学好,还会勾引人。可杨妮知道,勾引住她的只是那一片一片的青果干儿。
大学二年级之后,闺密就离开她了。小芳的原话是,唉你们俩就像骄阳,我这棵小苗把怕被晒死啊。虽然是玩笑话,可杨妮知道,那时候两个人粘的很紧,上课、吃饭、逛街,都是如同一个人。这个样子像极了包裹苹果的塑料布和青果儿啊,谁也离不开谁,虽然埋在土里,四周全是黑,但却很温暖。
大学三年级的时候,杨妮想要考研。那个人说,考什么研啊,又要等三年,我等不及了,于是杨妮放开胆子和那个人疯玩。小芳说,妮子,你堕落了唉,你妈不会打你吧。杨妮说,没事,打残了,有人养着就行。
大学四年级临近毕业的时候,杨妮签了一个外省大城市的单位,班里好多人都很羡慕。那个人知道了,对杨妮说,我是独子,我妈说离家近一点能照顾他们。要不我帮你联系单位吧?杨妮点点头,赖在那个人的怀里,轻声的嗯嗯。
小芳知道了这件事,指着杨妮的鼻子,气急败坏的说,妮子,你是个傻子呀,这么好的工作都丢了,我要是你妈,就打断你的腿。杨妮搂着她的脖子,笑着说,还好你不是我妈,不然的话,我都死了八百遍了。小芳唉声叹气,哭丧着脸说的,死妮子,你会后悔的。杨妮却笑了,心里说,怎么可能。
工作两年之后,在那个小小的县城,杨妮穿上了婚纱,和那个人走在一起。那天好多同学都哭了,可哭的最凶的是小芳。她搂着杨妮,走到那个人跟前恶狠狠的说,你听着,杨妮要是少一根头发,我就会剃光你的脑袋。那个人拉着杨妮的手,一脸幸福,拍着胸脯向小芳保证,绝不会少一根,负责他就自己拔成秃子。杨妮也哭了,可心里很甜。
结婚两年后,宝贝出生了,没有房子,没有暖气,奶粉也只能喝能喝的。杨妮抱着孩子在冰冷的屋子里裹着被子取暖,那一刻她有点想哭。可那个人说,妮子,苦了你了,我会努力赚钱。今后啊,你想到那儿买房都行,想给孩子喝什么奶都成。杨妮又哭了,泪水有点涩,但仔细尝尝还是甜甜的。
孩子两岁的时候,买了房子,是小城里最好的小区,南北通透,向阳温暖,忙碌了大半年,终于住了进去。
在新房的第一顿饭,是三个人吃的,只是简单的三菜一汤,可杨妮吃出了五星饭店的味。摸着宝贝女儿的脑袋,笑着说,终于有家了。
那个人,那天喝了点酒,抱着女儿疯玩,又抱着娘们俩说,我们三个相依为命啊,今后幸福的日子多着呢。女儿在傻笑,杨妮也在傻笑,那个人在偷着乐。小芳打来电话,连声道歉,她准备出国,来不了,但最后却说,让杨妮把眼睛擦亮点。杨妮却不懂,自己五点零的视力,不需要擦,还笑话小芳,别成了剩斗士。
孩子上小学的时候,杨妮第一次哭了,她不放心这么个可爱的小人儿一个人孤单。那个人站在杨妮对面,冷着脸说,一个妇道人家,总是婆婆妈妈的,孩子大了,就要会飞才好。杨妮哭着想靠上去,那个人立马离开一步,还说,你这像什么样子,这么大年龄了,丢不丢人啊。
那天回家,杨妮一个人躺在床上哭了,给小芳打过去个电话,她没接。很快她又回了过来,电话接通了,小芳说,她在国外,开玩笑说能给杨妮省一分是一分。但听到杨妮拖着哭腔,她就急了。大声喊着,妮子,你等着,我忙完了就回去看你,等着我不揭了他的皮。杨妮笑了,说还是小芳好啊,我等着呢。小芳说,你还笑,傻了吧,让你擦亮眼睛你不听,唉。
宝贝女儿上三年级的时候,杨妮和那个人分床睡了,屋子很大,床就有四个。女儿好奇的问,妈妈你们为啥要分开睡呢?杨妮想哭,还是忍着泪说,宝贝乖啊,你爸白天太忙,两个人睡他休息不好,影响工作。女儿信了,可杨妮自己都不信。他问那个人,他说,唉年龄大了,呼噜声太大,怕影响你休息,杨妮勉强让自己相信。她不想再给小芳打电话,因为小芳也结婚了。
女儿五年级的时候,杨妮第一次发怒了,但却没有破口大骂,更没有暴跳如雷。出差回来的早了一天,推开卧室的门后,她就后悔了。因为床上纠缠的两个人其中就有那个人,另一个是年轻时自己的影子。
那两具白光光的肉亮瞎了她五点零的眼睛,小芳说得对,好多年前,她就是一个瞎子。那嗯呀的缠绵声刺破了她的耳膜,好多年前,妈妈的话早就从那个破了的小洞里溜走了。
她就静静的站在门后,用瞎了的眼睛和破了洞的耳朵,看着、听着近在咫尺的荒诞。扭曲着,哼叫着,那个人的肥肉一圈一圈的震颤。杨妮想起小时候,过年杀的肥猪,又白又圆,就是没有生机。那个娇小的自己的影子在肥肉下扭动着,斯嚎着,直到看到杨妮晃瞎了的眼射出的黑光,一切才开始恢复正常。
那个人慌乱的赤裸着一堆白肉,就这么赤条条的向着杨妮冲来,嘴长的大大的又快速的闭上,似乎在大喊着骂人的话,可杨妮的耳朵聋了,什么都没能听到。
瞎了的眼睛收到一个重击,杨妮就倒下去了,她想睡着了也好,就这么过去,吧,可还是醒来了。而且眼睛也不瞎了,耳朵也不聋了,她看到两双腿和两只脚从自己的头顶迈过,她听到那个人对着自己的影子在缠绵,就像好多年前的那个傍晚。
这件事过后的一月,小芳给了那个人一个大大的响亮的耳光,她还是食言了,没能剃了他的头,让他变成一个秃子。
小芳说既然他不仁,就别怪我不义。按她的道理,那个人只有净身出户一条路,可杨妮却不愿意。她知道自己的心里除了女儿再也存不下这个家的一根针大小的东西,哪怕是暂时的,她也怕再染黑了自己的手。
于是在六年前,杨妮和女儿回到了家乡。房子是租来的,工作是临时的,可日子却慢慢的有了生机。女儿问,是爸爸不要我们了吗?杨妮说,不是,是妈妈想给你一个好的故乡。女儿似乎懂了,可杨妮知道,自己是真懂。
小芳现在在一所大学里任教,她老是打电话说,嗨,妮子,你猜猜,今年我遇到谁了?杨妮笑着不语,她就急急忙忙接着话头说,我们俩啊,你不知道,今天来的一对新生像极了我们俩的样子,我以为我是眼花了呢。杨妮默默的流泪,她知道,远处的小芳此刻也是泪流满面。
桌上的青果儿,女儿很爱吃,杨妮知道,该找个日子给孩子讲讲这青果儿成熟的过程了。因为它就是自己这么多年来活在世间的一个模具,对就是一个模具,能吃的那种。
喜欢的话,互粉啊!
契诃夫写的一篇小说《万卡》,小学时曾经学过这篇课文,印象题目是《写给乡下爷爷的一封信》,如今仍能想起这个故事,至少说明这个故事能够经得起岁月的考验,应该算是好故事。
三个月前,九岁的男孩万卡被送到鞋匠家做学徒。在圣诞节的前夜,他没有上床睡觉。他等到老板、老板娘、几位师傅出去做晨祷以后,就从老板的立柜里拿出一小瓶墨水和一管安着锈笔尖的钢笔,然后在自己面前铺平一张揉皱的白纸,写起来。他在写下第一个字以前好几次战战兢兢地回头看看门口和窗户,还斜眼看了一下那个乌黑的神像和神像两边摆满鞋子的架子,然后他自己就趴在凳子前开始写了起来“亲爱的爷爷,您好!我在给您写信,祝您过一个快乐的圣诞节,同时祝您万事如意!我没爸没妈,只剩下您一个人亲人了。”万卡朝黑暗的窗子看看,玻璃窗上映出蜡烛的影子。
万卡叹口气,拿钢笔在墨水里蘸一蘸,接着写下去:“昨天我挨了一顿打。老板揪着我的头发,把我拖到院子里,拿皮带抽了我一顿,因为我摇他们那个睡在摇篮里的小娃娃时,一不小心睡着了。上个星期有一天,老板娘叫我把一条鲱鱼收拾干净,我就从尾巴上弄起;她就捞起那条鱼,年鱼头直戳到我的脸上来。师傅们取笑我,打发我上酒店去打酒,怂恿我偷老板的黄瓜;可是老板随手捞到什么就用什么打我。吃食呢,简直没有。早晨他们给我吃面包,午饭是稀粥,晚上又是面包,至于茶啦,白菜汤啦,只有老板他们才大喝而特喝。他们叫我睡在过道里,他们的小娃娃一哭,我就别想睡觉,需要不住手的摇那个摇篮。亲爱的爷爷,您发发慈悲,带我离开这儿回家去,回到我们村子里去吧;我再也受不了啦……我给你叩头了,我会永远为您向上帝祷告,带我离开这儿吧,不然我就要死了……”万卡嘴角撇下来,举起黑拳头揉眼睛,抽抽搭搭地哭了“我会替你搓碎烟草,要是我做错了事,那就像打那头灰山羊似地打我好了,要是您认为我没活儿做,我可以去求总管看在上帝的面上让我给他擦皮鞋,或者替做牧童也好啊。我原想跑回我们的村子去,可是我没有靴子,我怕冷。等我长大,我会报这个恩,养活您不让人家欺侮您;等你去世,我一定要祷告,求上帝让您的灵魂安息。”
万卡不由自主停下笔来,想起了爷爷。万卡的爷爷也在给别的老板打工,职业是个守夜人。那是个瘦小的、然而非常矫健灵活的小老头,年纪约莫六十五岁,老是带着笑脸,陝着醉眼,白天,他在仆人的厨房里睡觉,或者跟厨娘取笑,到晚上,就穿上肥大的羊皮袄在老板的庄园四周走来走去,敲着榔子。他身后跟着垂下头的老母狗泥鳅。爷爷休息的时候喜欢抽烟,也喜欢把梆子挂在腰带上。爷爷喜欢带着他给老板干活,在不给老板干活的时候教他认识字和数数。他和蔼可亲极了。
万卡把写满字的信纸叠成四折,放进一个昨天晚上花一个戈比买来的信封里面……他想一想, 用钢笔蘸了蘸墨水,写上地址:寄交乡下爷爷收。拿起写好的信,万卡戴上帽子,顾不得披羊皮袄,只穿着衬衫,跑到街上去了。昨天晚上他问过肉铺的伙计,伙计告诉他说所有的信都该丢在邮筒里,由醉酿醺的车夫驾着的邮车装走,响起铃送到世界各地去。万卡跑到就近的一个邮筒,把那封宝贵的信塞进了筒口… 万卡抱着美好的希望而定下心来,过了一个钟头,就睡熟了。……在梦中他看见 一个炉灶。爷爷坐在炉台上,耷拉着一双光脚,给厨娘们念信。……泥鳅在炉灶旁边走来走去,摇尾巴。 这是这个故事的主要内容。今天印象仍然比较深刻,算个好故事。
昨天我三个姨娘一起从济南赶过来,原因就是为了和舅舅照一张全家福。
舅舅不久前查出癌症晚期,属于他的时间不多了,这两天再次来医院做化疗。
我带着老妈在做化疗以前赶往医院,就为了和舅舅舅照一张全家福。
我们到了医院,舅舅像个孩子一样,看到自己的亲人,热泪盈眶。
妈妈和姨娘还有舅舅总共姐妹五个,他们疼爱舅舅就像自己的孩子,知道舅舅的病情,他们承受不了沉重的打击。
姨娘们日夜思念着舅舅,不时的过来看看,昨天我也了了她们的心愿。
表弟用轮椅推着舅舅,和姨娘们一起到楼下的公园,找风景好的地方,我们把舅舅扶到秋千上坐着,妈妈和姨娘坐在两旁,小姨娘在后面。
我酷爱照相,也让他们尽情享受照相的感觉,各种不同的角度教他们摆出不同的造型。
我把照片发到我们老表们的群里,心里又高兴又难过。我让姨娘和舅舅看我的杰作。
舅舅一句话把我们逗笑了,然后又哭了,“不是你拍照片技术好,是我们长得好。”
陪伴舅舅的时光,快乐,难过,痛并快乐着。
想来二十多年过去了,梅子在干什么?她还在人间吗?倘若还在,她幸福吗?
其实,整个村子都不知道她真实的名字,大家只是习惯地叫她梅子。
那年,我在临村的一所学校教书,每到周末便回到家里。
我所居住的小村湾名叫老李湾,是一个古老的湾子,据说已有400多年的历史。
打我记事起,便见我的村湾由朝东朝南的两排房子组成,它们构成了一个“厂”字形。这样的形状历经十多代先人一直未变,直至今日。并非这里没添人丁,改建房屋,只是搬出迁走的多,以至于今日显得愈加凋零。
我的家在朝东的最北头,梅子的家朝南,恰在“厂”字形与东排房子的交接拐角处。
日落黄昏时分,我打开后门,来到后菜园,便每每能看到她。
只见她只身向二三里地的集市方向眺望,那眼神是期盼的,圆圆的脸蛋上布满了愁云。
那时,我还是单身,对年轻女子总想要多瞄上几眼,特别是像眼前这漂亮的。
她是一个令所有男人都喜欢看的女人,身上并没有特别突出的地方,但每一处又都让人看了舒服。中等个子,不高不矮,身材匀称,不胖不瘦,圆圆的脸,既不向上拉起,显得下巴略尖,也不向下耷拉,显得脸肉臃肿。就那么恰到好处,要不是脸蛋略显黑一些,我想极有可能成为“上品”。
这后菜园历来所见是瓜菜、飞鸟、昆虫,起初看见她,我好生诧异,在这样的地方怎么会出现这样一个尤物?
我进得门来问父母,他们说:“你知道原先在那房子里住过的四婆吗?”
“哦!”我想起来了,儿时常见到过的一位矮而胖且佝偻着腰的慈祥的白发老太婆,我曾多次地叫过她“四婆”。
父母说;“她叫梅子,就是四婆家四儿子第三个孙子的媳妇。”
说来与我还是同辈,她的丈夫我也见过。前些年知青下放,他家几姊妹兄弟都回了老家,就在这老屋里炊炊打打的十分热闹,把从汉口拉回的锯末子压成如蜂窝煤般形状的,用来做烧火做饭的燃料。倘若在族屋里攀亲的话,我得叫梅子是嫂子。
但在城里住着享福不好,为什么要到乡下来吃苦呢?我一直纳闷。后来时间长了,我便知道她的一些事情。
据说,她的家乡原本在宜昌,四婆家的三孙子全乔是长江上的驾船工,常常货运到宜昌,便在梅子的家旁落脚住宿。
这样,梅子就和全乔认识了,时间久了,梅子便跟全乔来到了武汉。
那时梅子才十六岁,说白了,是跟着全乔私奔了。
再后来,梅子就跟全乔生了一个水水灵灵的女儿。
这私奔的婚姻到此也能称得上是美满的,梅子终究奔来个能在大城市稳定安生的结果。
可安稳的日子没过太久,街道上就起了说梅子与人乱搞的风声,当全乔两月三月或更长时间回家一次时,便被这风言风语压得喘不过气,时常会与她大吵大闹。
每次,梅子都会虔诚地悔过,每次都信誓旦旦地赌咒没有下一次,每次都在丈夫几天休假的温柔满足里反思自己的过错。
但还距二十岁也远,还尚不足成熟的梅子,在汉口的花花世界里,稚嫩的心和躁动的青春,及渴望男人的漫长岁月里,难抵那些诱惑的甜蜜。时间长了,便又听到她被男人搞的事情。
实属万般无奈,于是全乔一家就借口汉口的房子紧住不下,把梅子娘俩送回老家居住了。
我这才想起前不久,打全乔几姊妹兄弟回城后,闲置多年无人居住的房子又急急忙忙修缮的事。
梅子母女回到老李湾后,因母女都生得人美嘴甜、落落大方,一时是蛮逗湾里湾外的老老少少喜欢的。特别是那小丫头,灵气活透,加之服饰新颖别致,与乡里娃的土衣布衫、拘谨呆板相比,那是洋气、阳光、泛着朝气。
梅子是不会干农活的。刚到老家时,村里也给她分了口粮田,但她不会种,只是挂她的名,耕耘栽种收割都是近族帮忙。
我本家的侄子方代在村里做书记,他见这么着不是回事,便把梅子安排在村小学校里烧饭去了。
村里的小学校实在太小,只有七八个老师,真正在学校食堂吃饭的也就两三个人。两三人的伙食,自然要不了多少时间便能安排妥当。
梅子有太多的闲暇,这闲暇闷得她不知道怎样打发为好。
她天生就不是闺宅中的那种,她在宜昌,长江的浪伴她疯长成少女,来到大汉口,人潮、霓虹、三教九流,开始在她初为少妇的血管里奔流,她从来就没有寂寞过。
起初,她独自一人在只有磨盘大的小食堂里发呆,心里想着她那该死的,两三个月甚至更长时间才回家一次,她感到空虚寂寞的难以忍耐。
时间久了,她便在学校四周走一走,偶尔去学校前面的湾子里和婆婆、大婶、大嫂们聊聊天。晚上她便回到自己的家里,只有她与孩子的一个空旷沉闷的大屋子,脱衣上床,在被子里偎依着孩子,在梦里想着她那个该死的,那个找了各种理由把她弄到这个偏僻闭塞枯燥的要死的小村子里!
这样的日子也许有好长一段时间。
之后,她常去的便是学校前面的小湾子,去的最多的是一个叫花婶的家里。花婶是一个发福过渡的老女人,梅子随意的性格,到哪都叫人欢迎。花婶自然也喜欢上了她,还时常拿些苕片、豆子的小零食款待她。
花婶家有两个儿子,都长得五大三粗的。大的在外地工作了,家里就剩一个刚满20岁的小的。不多久,梅子就不知怎的和这小的勾搭上了。
有一天天刚麻麻亮,父亲从后菜园进屋来,自言自语地:“这么早,咋一个提着公文包的小伙子就从后菜园的缺口出去,顺着秧田的小路走了?”
后菜园及后菜园外的秧田小径均不是行人所走的路,这大早出现的小伙子,是干什么的呢?一家人都在纳闷中,但答案几天后就揭晓了。
那天中饭时分,信知便带着她梯形似的队伍(一母五女)端着饭碗来到了我家,我家饭桌上本不多的菜眨眼就没了。
信知家住在离我家三家处,也朝东,正好与梅子家交角。信知待坐定后,便扯着一个大喉咙嚷开了:“哎呀呀,我家放在墙边的那个大砂锅,今天一大早被一个小杂种踩破了。我听到响声赶出门时,那小杂种已到前面的塘塍上去了,也没看清长的是个啥逼样?”
簇拥在信知旁的丫头中的大丫头抢话了,说:“我看见了,那个人是从梅子家出来的。”
于是大家便都心领神会,心知肚明,都默不作声了。
信知知道这事是不能乱说的,便佯装发怒地朝大丫头吼一声说:“谁说你看见了,那是你眼睛发花看见鬼了!”
但此后的不多久,“踩破砂锅的事”就像长了脚似的,便在满村子里传开了。
捕风捉影这样的事毕竟是不能胡乱瞎说的,得有真凭实据。
但在后来的不到两月里便有了结果。
听说全乔并没有像往常那样在日落黄昏时回家,而是在深夜突然出现在梅子的床前,把梅子和这小杂种逮了个正着。全乔还当场叫这小杂种写下“证据”,以至这证据成了日后离婚的重要凭证。
梅子在被送回老李湾时,他的近族都知道她是怎么回事,但远族并不知道,只是心里在揣度,现在大家便都知道她回老家的原因,都知道她是一个偷人的,没有男人就不能过日子的女人。
但村里的女人却并未过多地指责她,是她已太没价值或是太不要脸了,不值得她们去指责了,或是她们在心里着实同情她?梅子正是年龄,而全乔那么长时间才回来一次,怎不偷呢?
村里人过多地都在咒骂着花婶的儿子。怎就年纪轻轻地跟一个少妇搞上了?听说他还谈了女朋友呢?这人家姑娘还肯要?
总之,都在骂这花婶的小儿子不是个东西,骂这个没志气的东西还活着干什么,不如死了算了!
没过多久,全乔与梅子就离婚了,全乔把女儿也带到汉口去读书了。梅子离开了小学校回到了这时应该说已不算是她家的家里了,大多时间憋在屋子里,偶尔也在湾子里走一走。
当这风流韵事在大家的口中轮番品尝腻了后,反倒湾子里的老老少少也就再没有了过去般对她的指指戳戳了。
那段时间,她的近族便到处张罗给梅子一个归宿。离婚了,已与李姓湾子里的人没什么联系了,但总得要把她安排到一个地方去,不能让她老死在这里。
小虎,曾经和我同过学,住在朝南最西头的一家。前几年顶他爹的职到汉口工作了。可手脚就不那么干净,在厂里做保管把东西偷了不少,坐了几年牢,刚放出来,年龄也不小,算来也是同辈。她的近族便张罗给小虎说上。
此时的梅子已六神无主,除了年幼的女儿,除了精神的依托不能给她分担一点的女儿外,再也找不出一个亲人来为她的未来和命运或分担或作主。只能是,别人说怎么样她就怎么样,别人说怎么着她就怎么着。
后来听说小虎从汉口回来和梅子住了三五天,便再也没有音信了。我的嫂子替梅子有些愤不平,叫梅子去找,叫梅子去说她早取环了,现在怀孕了,要小虎负责任。但梅子终究没那个勇气,便默默地不作声罢了,时间长了,便再也没人提及了。
她的近族仍在不懈地努力为她找一个人家,终于在临村找了一个刚死去老婆的男人,很快梅子便嫁了过去。她的近族人终于有了如缷下一副沉重担子的快感,轻松了。
后来,湾里人说,梅子为那个男人生了一对双胞胎儿子,还时常看见对面田野的田塍上梅子牵着一头大水牛在放,但她从没越过田野的界限到老李湾这边的田塍上来。
最后一次听说梅子的事是她女儿在汉口得了白血病。女儿在临死时,全乔把梅子接到医院看女儿。听说那次梅子哭得很厉害,晕死过去好几次。
她的女儿走了,她对李姓的家庭就什么也没有了,她三十几年的时光就全空了。
我时常在想,梅子还是否牵着那头大水牛在对面的田塍上放呢?
她十六岁就跟了全乔,在花样慒懂的年华背叛了家,至今都未回过宜昌,没了爹娘;后又从汉口流落到乡下,没了女儿;嫁给一个比自己大十多岁的男人生儿育女。她的前半生什么也没有,最终成为一个任人摆布的木偶。
这一切是她自己造成的,还是别人?
--The end--
作者:碧 峰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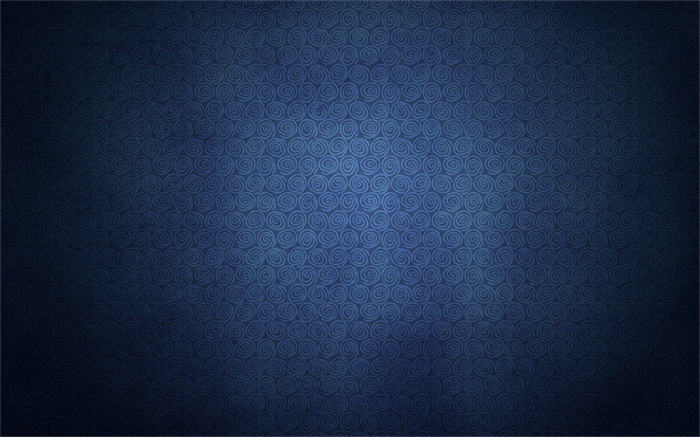

未经允许不得转载:婚纱_礼服_秀禾_旗袍_婚纱礼服-顺长婚嫁网 > 有什么故事值得分享?
 有什么故事值得分享?
有什么故事值得分享? 哪里可以买到黑色的婚纱?
哪里可以买到黑色的婚纱? 郁金香与猫什么意思?
郁金香与猫什么意思? 如果用两个字形容你人生所经历过的岁月,你会用哪个词?
如果用两个字形容你人生所经历过的岁月,你会用哪个词?















热门信息
阅读 (4)
1 谢娜出局会离开湖南台?风光不再,和张杰的婚姻还能稳定吗?阅读 (3)
2 婚纱照mv故事梗概?阅读 (3)
3 247代表什么意思?阅读 (3)
4 木樨园百荣有订做婚纱,敬酒服的吗?阅读 (3)
5 大部分中国新娘为什么钟情于白色婚纱?